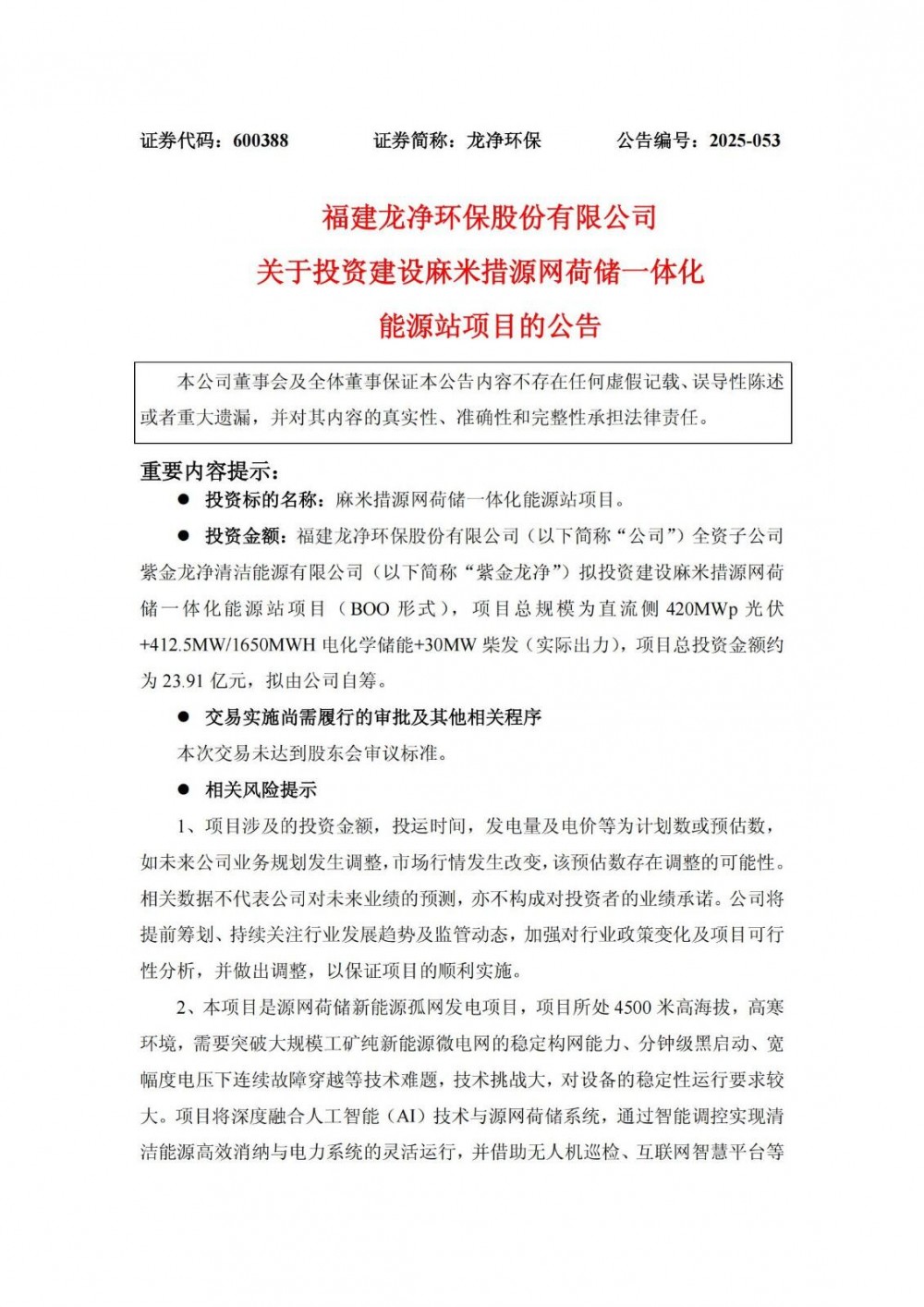遇到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类需要一个发达国家承担历史和现实责任的时候,美国民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缺少勇气和担当精神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库珀(Richard Cooper)有一次在谈到关于全球气候政策时,曾对我说:“即使2000年戈尔当选了总统,我想他也不会签《京都议定书》。就这个问题来说,布什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位精通美国政治运作的前副国务卿能够作出如此判断,确实是有原因的。
6月底,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终于跌跌撞撞地以微弱多数被美国众议院通过。下一个议程就是期待不久之后美国参议院的表决。舆论预测参议院否决该法案的可能性很大。
再来看看美国参与国际气候条约的情况。在美国大选前夕,奥巴马曾对英国《自然》杂志说,“我承诺美国将重新加入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新条约。到那时,美国总统将再次面对国会对此国际条约的审议。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里(John Kerry)最近已经表示,即使参议院通过了国内的减排法案,也不一定会批准国际条约以约束缔约方国家实现减排承诺。一旦国会否决美国签署这项国际条约,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宣布退出《哥本哈根议定书》。
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国家。无论政治家们在竞选前如何鼓吹听起来很高尚的理念,在真正履行他们的权力时,选票和集团利益仍然是两根最重要的指挥棒。
首先是选票。美国选民习惯了浪费资源的舒适生活方式。政治家们虽然在竞选时大谈环保主义,但如果真的为了保护环境向选民开刀,比如征收环境污染税或燃油税,他就很有可能失去一大批选民的支持。而即便一项温室气体的减排措施不会直接增加选民的生活成本,议会成员仍会因为法案对选民造成潜在损失而拒绝支持减排法案。共和党众议员赫勒(Dean Heller)就声称该限制排放措施可能使他的选区失去5500个工作岗位而在众议院辩论时号召其他众议员反对该法案。
其次是地方利益。我们拿新通过的减排法案来说明。比如,美国南方一些州是重点火电基地,火电是这些州重要经济来源,但火力发电主要用的煤炭也是污染和碳排放最严重的燃料。从具体条款来看,新法案只规定了对现有的减排步伐缓慢的电厂实行强制性排放上限,并对那些2009年后投入使用的新能源发电厂制定排放标准,要求减排50%以上。但该法案没有给任何现有的发电厂制定排放标准。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措施,是对南方地方利益的一个巨大妥协。
但是,即便如此,在地方利益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的参议院,对火电厂的减排措施将面临来自南方参议员的更强烈反对。目前,大部分对此法案“未表态”的参议员都集中在南方各州,这些州的参议员们正在等待新的妥协措施来进行地方利益交换。
第三是大公司大财团的利益。长期以来,美国的大公司和大财团对美国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是政治献金合法化的国家,法律也规定政治家们筹款的款项和来源等信息必须公开。这一制度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每个政治家,从总统到议员、背后的企业财团利益。
就拿这次新通过的减排法案来说,减排法案专门设计了一个逃避责任的“后门”——抵消政策。抵消政策允许那些不能直接减排的工厂通过在其他方面作出努力来获取同等的碳信用额度。抵消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美国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它们可以通过实施抵消项目,如帮助农民捕捉动物粪便和池塘中的甲烷,来获得与其他减排工厂一样的碳信用额度。由于那些抵消项目的成本要比购买碳排放权或安装新型节能设备要便宜许多,这一抵消政策为大公司提供了相当大的逃避承担减排成本的空间。
而且,即便大公司采取了抵消措施,那些措施也未必真能达到同等的减排效果。有学者发现,在《京都议定书》实施了类似的抵消政策后,富国在穷国开展的许多抵消项目最后都变成了“虚假项目”,或者减排的实际成果远比宣传的要少得多。
美国的民主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典范,民主制度也确实造就了200多年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但在遇到诸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类需要一个发达国家承担历史和现实责任的时候,美国民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就缺少那种勇气和担当精神。他们为了选票和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往往会作出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决策,从而把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置于脑后,并将减轻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重要的是,美国的表率作用还会使得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效仿。前不久,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进展有限”,最主要原因就是各国都在观望美国国内的立法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利益绑架了的美国政治家,甚至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障碍。
 中国能源资讯网
中国能源资讯网